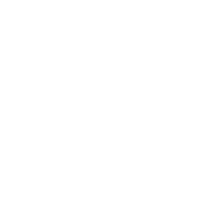
元煊在线(父皇开门,孤要登基)最新推荐_最新推荐元煊在线(父皇开门,孤要登基)


这称呼许久未有,那时候小儿夜哭不能止,太后抱了她在佛堂前,灯火煌煌,在燃灯佛前唤道“灯奴儿,莫要哭了。”元煊真不哭了,隔日太后给她取名为煊,取日光赫赫之意。只可惜许给了过去佛,她也不必做现世奴。“一应证据都存在我这里,祖母可要看?”元煊隔着锦帐应了一声。“不必了,叫严伯安去颁布诏令便是。”元煊点了头,转头出了殿,吩咐旁人,“给我做一碗酪奴来,一夜没睡,没力气得很。”
暮色四合,浓云欲坠,佛寺参拜的人早已四散,小沙弥跑来跑去点着灯,功德箱里哗啦啦倒出来五铢钱,一旁的当家正在监督小沙弥将钱收拢好,手上的账册记载着今日大檀越捐来的布帛。
“这些商人真见利忘本,今日有人捐了百匹布,我验看了一匹,居然尺度不足,难怪佛祖不庇佑。”
“如今这五铢钱是越来越不值钱了,粗劣得很。”小沙弥抓了一把铜钱,摩挲了一下,确定这都是民间私造的铜钱,胡乱塞进麻袋里,哗啦啦作响。
“就是再不值钱,那也要收起来,仔细着点,别落下一个字儿,要不有你好看!”
侯官闯进来的时候,僧兵们尚没来得及反应。
元煊只找佛寺的监院,带着人直入佛堂,问了一句名字,“景明寺监院契沙和尚?”
那当家一怔,“是我……”
眼前人瞧着来势汹汹,且已近宵禁的时候,能在街上走动的只有巡逻的官兵,可这帮人着装齐整,却并非平日里所见的禁军。
尤其那带头的人,一身缁衣,倒像是那些寺庙里静修的居士。
难不成,已经有起义军打到洛阳城来了?
“你们是干什么的?!”
契沙和尚高声喊道,一面催着小沙弥,“快!快去喊僧兵!”
小沙弥想要溜走,功德箱本被倾倒着,见着阵仗赶紧松了手,木箱轰然落地,铜钱哗啦啦倒出来,泼洒了一地小铜山,这动静哪里能逃得了,被围了一圈的侯官拎着后脖颈拿住了。
“喊什么?喊破喉咙也不会有人来的。”那侯官捂了小沙弥的嘴,看向了元煊。
元煊笑了笑,还和和气气地回答了人的问题,“奉天命,上查宫庙,下摄众司。”
她取出一张盖了印的白纸,落到契沙和尚面前,“你道我们是谁?”
契沙和尚心里是有些不信的,佛教是大周国教,谁敢动他们寺庙里的人,更何况他们还是洛阳城里的大寺庙,多少大檀越都是累世的勋贵,对着他都要毕恭毕敬,管眼前的是虎贲还是羽林军,一身的土腥气,平常都进不了这佛堂。
可他定睛一看,慢慢僵住了,目光向上,对上一张秀窄深刻的脸,瞳孔印着他游移的惊慌,继而一声冷嗤,叫他从尾巴骨到头皮都僵了,转而去看身后的那些兵。
胸甲下衣襟口绣着白鹭飞鹰,禽类的眼睛灯油一照,往外泛着光,跟活了一般。
这会儿和尚慢慢回过味儿来,居然是白鹭的官服,他吓得哆嗦,不明白怎么惹了上头的眼。
“今查契沙和尚贷出僧祇粟,偿本过利,私吞良田,致使数千良民流离失所,沦为佃户,不敬天子,不敬佛祖,带走。”
契沙和尚瞪大了眼睛,“不可能!城阳王怎么许你们来的!我们这是佛门!太后怎么肯?你们是皇帝……皇帝派……”
元煊收了笑,手按在了剑柄上,“城阳王?天下事都要听城阳王的准许?”
她回头看了一眼侯官们,“你们都听到了?”
一队人齐声道,“听到了!契沙和尚说天下事都要城阳王的准许。”
元煊点点头,“以城阳王为主,视为谋逆,格杀勿论。”
“不是,不是,你们是谁!胡言乱语!我没有!”
元煊挑眉,耳边传来兵甲之声,“殿下!全部僧祇粟借贷的契券都找到了!”
另一队侯官已经从禅房中搜了一圈,在佛堂门口就报了信,元煊看了一眼那厚厚成箱泛黄打卷儿的契券,“带走。”
“朝廷办案,阻拦者,视为同党,格杀勿论。”一侯官低声喝道,看着那赶来的僧兵。
住持都没敢去,自己坐在禅房里头,颤巍巍点了香,在佛前念经,他只愿意研修佛法,对俗事一概不管,寺庙产业,都是监院当家,侯官来他面前念了一遭罪状,他也只能闭着眼睛念一句佛,说一句不敬佛祖,自然不必留在寺庙中,由着侯官将人拖走了。
僧兵还不知情,被一嗓子惊动了赶了过来。
“你不能杀我!快!拿下他们!”监院指着元煊人等高喊,“我不信拿人敢拿到佛寺里!”
和尚不肯就范,抬手挡了一侯官,就要冲向外头喊僧兵。
元煊没什么耐性,剑出鞘,金属震颤嗡鸣,她抬手,利落一剑。
刃入血肉,噗嗤一声,在不可置信的尖叫中,青年人拔剑抬脚将人踹出去,那胖和尚后头挨了一剑,被踹出去,栽入铜钱小山里,硌得他连滚带爬还要向前。
“抓起来。”
她眼也未眨,转身看向了那群僧兵,鲜血在剑尖顺畅滚落,在煌煌的灯火与佛祖慈和的注目下,一点点浸染青砖地。
“普天之下莫非王土,佛寺不是法外之地,侯官捉拿罪犯,不要阻拦,还要动的人,视为谋逆,听清了吗?”
沙哑的语调刮过众人的耳膜,僧兵们你看我我看你,一时沉默。
元煊凛然扫了一圈,眼神所到之处,僧兵不自觉地后退了一步。
“走吧,下一户。”
元煊甩了甩剑尖,身后侯官拖着几个负责管理借贷僧祇粟的僧人,跟着走入了茫茫黑夜之中。
几个皇家寺院不能抖搂出来一点,如今佛寺依附皇权,太后要抢先按下这事儿,就不能带累到上头,正是战时,京中不可动荡。
如今沙门统远在大同静修佛法,在京中昭玄寺的副官瞒报凉州服役之事,就该直接下狱。
暗夜最适合侯官便宜行事,该抓的抓,反抗的杀,很快一切归于寂静。
等到穆望连夜收到密报,一夜未眠,撰写完奏报,就等着日头一出,上书皇帝,元煊带着一身血腥气回了家。
更深夜寂,长公主到家净了手,另换了一身干净缁衣,鹿偈抱着那缁衣,一股子血腥气冲上鼻尖,还混着缭绕的檀香气。
“殿下快歇着吧,都快四更天了。”窦素抱着足炉想要进内殿塞进被子里头。
元煊坐在榻上饮了一碗热浆,顿了一会儿,“我就在这儿眯会儿,不必费那功夫。”
“殿下?”窦素急了,“外头那样冷,您休息不好,又要头疼了。”
元煊闭着眼睛,干脆耍赖往软榻上一仰,不说话了。
窦素没法子,挪了被子给她盖,顺便摸了下手,还滚烫着,这才放了点心。
元煊着了风,其实头该疼的,她怕自己头疼,在行事之前当着侯官的面儿喝了药。
太医开的药和穆望求的看着不一样了,可喝过之后依旧身上滚烫,脑子飘然,便不记得痛了,只是穆望的喝了人身子怎么都不太舒坦,坐卧不宁,但太医开的药喝了却疏散清爽,理智和力气都在。
先前半年在寺庙里当着穆望的面喝了,转头也给吐了,看似她喝了半年药,实则全给了青砖底下的木头根儿去了。
穆望送来的侍女走步都是宫里的规矩,嘴上还说是穆家的丫头,元煊咧咧嘴,权当听个鬼话。
药里有鬼,侍女也有鬼,元煊本以为这都是皇帝授意的,反正约莫是慢毒,一时不会死,喝那么一两次也无所谓。
谁知她回京后,太后叫太医给她探脉,却没说药的事儿,到让元煊怀疑起是不是里头也有太后的主意,这倒叫她一时不能妄动,时常在人前喝起那药来。
皇帝和太后两党派分得清楚,朝堂上都势同水火,皇帝和太后却不tຊ能这么算,儿子和阿母实实在在是一体的,皇帝下的令十有八九都是和太后商量好的。
她心里清楚,若她是太后,也不会放心一个声势差点逼过皇帝和太后的储君,哪怕她名不正言不顺,用药拿捏,用得放心,指不定什么时候就横死了。
谁都不想她好过,她也不想叫这些人好过,太后和皇帝,一个都逃不开。
今日在佛堂前那一剑,额角青筋被吵得一跳,她就厌了。
对着这群硕鼠,杀了也算了,也在侯官面前立了威。
先前一个个还当她是个寻常富贵公主,不叫她进地牢,今日见了血光,各个跟冬天树上哆嗦的雀儿一般,不敢再吭声了。
她浑浑噩噩眯了一会儿,脑子里从药想到朝局,也没彻底睡着,等天光熹微就爬了起来,将手上一沓供状和改了的借贷契券以拢,赶着朝臣之前进宫去了。
太后还没起,披了衣服叫床上的人滚去了偏殿,隔着帐子喊了一句元煊的小名儿。
“灯奴儿,处理干净了?”
前头一句还带着长辈的亲昵,后一句就是上位者的询问。
这称呼许久未有,那时候小儿夜哭不能止,太后抱了她在佛堂前,灯火煌煌,在燃灯佛前唤道“灯奴儿,莫要哭了。”
元煊真不哭了,隔日太后给她取名为煊,取日光赫赫之意。
只可惜许给了过去佛,她也不必做现世奴。
“一应证据都存在我这里,祖母可要看?”元煊隔着锦帐应了一声。
“不必了,叫严伯安去颁布诏令便是。”
元煊点了头,转头出了殿,吩咐旁人,“给我做一碗酪奴来,一夜没睡,没力气得很。”
————
注:酪奴:北魏人好奶酪戏称茶为酪奴。

《陶云眠顾沂风》是一本不可多得优质小说,该书主要讲述了陶云眠顾沂风之间的故事,该小说讲述了:“好,我会的!”向来调皮叛逆的儿子,在洛清清面前乖巧得不像样。这一刻,陶云眠忍不住想,或许真的是自己这个妈做得太失败了吧。她苦涩低头,踏步进了屋。身后手打着绷带的顾沂风却也跟了进来。哐当一声门合上。顾沂风面色严肃看向她:“陶云眠,你最近到底是怎么回事?”陶云眠继续整理手上的行李包:“我不懂你在说什么。”紧接着,顾沂风单手夺过她手里的行李包,沉声问:“你之前是不是跟孩子说了,离婚不离婚这种胡话?”

《楚云卿萧溟》小说的在线阅读,该小说讲述了楚云卿萧溟的曲折故事,情节流畅,值得细品,绝不放手该小说讲述了:她曾经无数次的告诉萧溟真相,乞求他的相信,可他并未动摇分毫。楚云卿曾经为自己争取过,努力过,可现实却给她迎面浇了盆冷水,因为萧溟根本不相信她。既然争取不到,那便放手吧,连带着她十年的暗恋一起割舍干净。所以她是真心的祝福萧溟和司曦光幸福的。之前她在国外,天涯路远,他们不必再见。如今分别三年,也没有再相见的必要了。

傅浩宸邓玉婕的这本《傅浩宸邓玉婕》非常有趣,主角故事精彩,下面为大家带来章节片段:“......好,我答应你。”姜毅喉头滚动,艰难地应下了邓玉婕的托付。他从邓玉婕怀里接过孩子:“我安顿下来后,会给你寄去地址,但你要答应我,等你治疗结束后,你得给我和孩子,寄来明信片。”这边的医院只能检查出有脑瘤,但设备不支持探查是良性还是恶性的。邓玉婕能明白他是在鼓励自己积极治疗,于是轻轻点头:“我会的。”聪明的边牧似乎已经看出邓玉婕即将离开,不舍地围着她转了好久。

主角叫裴京越叶云岫的书名叫《裴京越叶云岫》,它的作者是佚名创作的总裁虐恋风格的小说,书中主要讲述了:叶琳使劲挣扎,她现在一刻都不想待在这里,不想跟这个杀人凶手再多说一句话,她怕自己会忍不住仇恨与他同归于尽。她尖叫:“放开,放开我。”程枫从来没见过叶琳这么丧失理智的一面,那时思容死的时候,她也只是安安静静的伤心流泪。而就在他诧异时,叶琳挣开他的手,跌跌撞撞地冲下楼去,独留程枫痛苦的呆站在原地。叶云岫反复烧了两天,等她再醒来时,浑身痛得好像被抽筋扒皮了一般,她强撑起虚弱的身子,嘴唇干得都裂开了,她四处看了看,才发现自己在医院里。